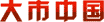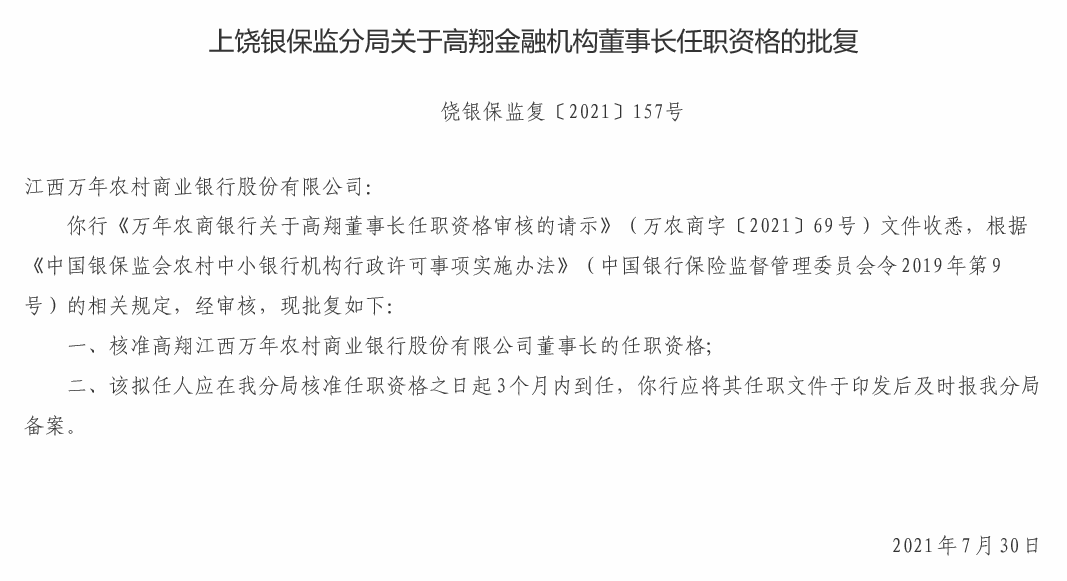从下西洋到大航海:“全球性”的阴影?
从下西洋到大航海:“全球性”的阴影?
文/(德)罗德里希·普塔克
明朝初期郑和远航的时代,由国家支持的航海活动,主导从南海到东、西印度洋的国际远洋贸易的一些分支路线长达约三十年,它使此前这一海域的各种海上活动相形见绌。
1405年—1433年,郑和率领七支船队下“西洋”,这片区域从占婆(又名占城,今越南南部古王国)经马来半岛和爪哇,直到印度洋周边国家和地区。据说郑和手下有两万到三万人之众,包括水手、士兵、官员、医生、技师等,士兵还拥有“火器”。郑和船队在海上曾和敌人遭遇,如果那期间使用过火炮,那么就必须对欧洲人才真正在海上进行过炮战的通行观念予以修正。
郑和船队 众说纷纭
在郑和船队频繁来往的地方,国家和地区的名称流传下来,不仅见于中国留存的碑文,也载于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巩珍、费信等人的历史地理作品。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朝为国家服务的船只在南京和东非之间的众多海域航行。虽然从前就有更小型的船队克服过漫长的距离,有时甚至将东亚和海湾地区或红海联系起来,比如波斯商人,但这些海上活动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于私人动机。
亚洲的贸易空间曾被分成由不同群体所使用的几个大区,明朝的船队剧烈地打破了这种结构,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亚洲政权在亚洲大部分海域当中展现存在感。当时,东南亚大多数沿海地区的居民数量显然少于一万或一万五千人。当巨大的中国船队抵达一个地方,哪怕只是载有三千到四千人的十到十二艘船,当地是如何解决他们的生活供给呢?流传的船员数量是否有误?也许船队的规模要小得多,或者在供给上自给自足。
后来声名显赫的马六甲,那时候不仅居民较少,而且刚从晦暗的历史中走出来。另一面,当郑和与他的手下官员见到马来半岛上各个地方的建筑主要是小木屋,也许他们会认为这些地方极端落后。因为明初的中国,已经拥有不少有防御功能的坚固城墙环绕的城市,城里修建了学校、街道、桥梁、仓库市场和各类管理机构。
明朝巨大船队真正的作用和使命也是一个争议话题。这些船上确实运载着士兵,以便在危急关头实施武力进攻。但同时,船队还运输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商品,返程时购置香料、热带木材、药材、异国珍兽等贵重货物,以带回中国。此外,船上一直有外国使节,代表其君主奉上贡物。因此,郑和船队的主要任务是贸易和外交,少部分是军事。在军事层面上,早期的明朝有别于欧洲一些后来者,这些欧洲人虽然同样追随贸易兴趣而来,但在必要时更频繁地动用武力。
中国拥有更多的船只和人力,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郑和的船队很可能在远洋贸易上占据了主要的份额,而沿海贸易则留给了欧洲人等后来者。还有毫无争议的一点是,明朝的国家航海行为和欧洲殖民时代的行动不同,它并非为了传播宗教观念,不具备传教的元素。
1433年,郑和的海上壮举正式开始三十年后最终停止了,中国也完成了其漫长历史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篇章。这是一段成功的历史,为何竟陡然终结,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约八十年后,马六甲仍希望中国帮助它对抗来犯的葡萄牙人。显然,15世纪的明朝在有些地方还长久地享有强大保护力量的声誉。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时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几种文献中还提到过中国国家船队在亚洲的影响,它们让人感受到,中国航海达到了使人印象深刻的规模,持久地影响了同时代人的记忆。
航海活动:文治还是武功?
明代中国退出世界海洋的行为还有另一个特征:它并非受到外力的胁迫,而是出于内部的权衡。而其他的航海大国往往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受到对手的驱逐而成为悲惨的输家,不得不离开舞台。明朝的退出单纯是出于自主选择。正因为如此,明代早期的航海活动早已被视为和平崛起、经济增长和文化交流的表达,中国希望以此和英美世界的帝国主义诉求划清界限。
探讨15世纪初明朝航海系统和葡属印度之间的差异,可以从动机开始。葡萄牙最初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种寡头统治,但从来没有实现过。要实现垄断,葡属印度还过于弱小,即使在权势鼎盛之时,它也只拥有数十艘船,定居亚洲的葡萄牙人只有一万到两万。而在明代早期的航海活动中,很难看到存在类似的寡头设想。
对战略上重要的地点和地区,这两个体系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马六甲、苏门答腊岛北部、卡利卡特和科坎、马尔代夫、霍尔木兹和亚丁。葡萄牙人征税或力求实现全面控制,但他们不能永远成功,也没能到处如愿。中国满足于朝贡关系或名义上的臣服。明朝也维系着有官方代表驻扎的据点,但和葡萄牙治下的一些地方不同,中国的这些贸易分部无论具体形态如何,均不需建立军事防御工事。
欧洲列强之所以有能力在亚洲立足,占据东亚贸易的一部分并获取据点,是由于其技术优越性。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论据。装备大炮,便于驾驶的船只,探索大西洋世界过程中获得的全面航海知识,都可算是他们手中重要的王牌。但我们在下结论时必须谨慎,因为在军事上,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并非在任何地方都胜过亚洲人。16世纪初有足够多的资料说明,中国沿海船队非常善于应对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船只。事实证明,欧洲人的据点绝非不可战胜。比如17世纪的荷兰人就在台湾遭遇了失败。因此,把扩张能力单纯归根于军事优势并不恰当。
暴力在明朝和葡萄牙所代表的这两种体系当中究竟有何意义?历史已经证明,在亚洲海洋当中,战争、掠夺、海盗等现象古已有之。元朝入侵未遂、倭寇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明朝的国家航海运动大多和平进行,也不能完全脱离武力,更不必说葡萄牙人了。也许是为了展示自身的强大,葡萄牙的一些史料甚至好战地大肆吹嘘和渲染某些冲突,或意图将其解释为驱动力,显然是把结论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或者带有倾向性。
与早先的葡萄牙人不同,荷兰人和英国人更愿意隐瞒甚至掩饰其暴力行为,事实上他们却连续发动战争,实行大屠杀,不断抢夺新的领地。
“玛门朋友”与“教化使命”
葡萄牙扩张的特点是其背后既有世俗目的,也有宗教动机。其实,这种双轨制和欧洲的两极有关:里斯本和罗马。在所谓教会资助的框架下,罗马给葡萄牙委以特权,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义务。这些特权和义务的重要性不容小看。此外,教会还有其自身的“机关”,它利用葡萄牙的航海网络深入亚洲,影响范围往往超过葡萄牙贸易势力之外,西班牙方面的情况也类似。
重要的是,亚洲沿海地区此前从未出现过这一的现象。至少,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从未如此有目的地推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上级机关来协调统摄。因此,伊比利亚半岛两国所体现的这种机构化的双轨制,亚洲各国完全不具备。
来自基督教欧洲的荷兰、英国人和其他非天主教群体在1600年前后才出现在亚洲,对他们而言,传教工作最初只处于次要地位,只在自身队伍中进行,后来才发展到外界。由于天主教阵营是他们的敌人,从前根植于宗教的欧洲内部矛盾,即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就转移到了亚洲的海洋世界。由欧洲引导的“全球化”,也投下了“全球性”的阴影。
与欧洲相反,明朝没有使异族归化的意图,其状况完全和葡萄牙及西班牙不同。相对于冷静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明代早期航海框架下占优势地位的是思想因素,它涉及的是道德、秩序、和平共处。
在葡萄牙的航海活动中,上帝和金钱上演着二重唱。在这里,宗教取代了“文明”的位置。在荷兰人和英国人当中,“玛门朋友”(在教会话语里玛门是掌管财富的伪神,贪婪原罪的象征,此处指财富)成了宗教的替代物,一切道德销声匿迹。
有观点认为,商贸实践及其背后的银行体系、信贷体系等,为欧洲人在亚洲贸易的成功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葡萄牙体系内部以及后来其他欧洲人筹措资本之快速,是否应被看作让欧洲人领先于其亚洲竞争者的要素,似乎仍然有待商榷。我们不能忘记:几乎一切在亚洲的欧洲组织都周期性地缺乏资本,必须依赖亚洲资助方的贷款。
直到荷兰人和英国人登上舞台,才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他们长期把在亚洲的事业当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来经营。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一种被赋予各种法权的股份制公司,这些法权堪比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
本专题作者为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内容及部分图片选编自《海上丝绸之路》中文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10月版),译者史敏岳,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转载已获后浪出版授权。